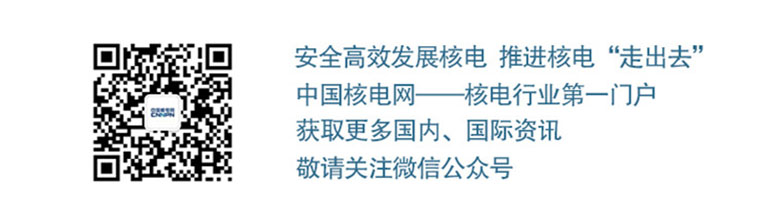當地時間6月22日下午,國務院總理李強在巴黎愛麗舍宮會見法國總統馬克龍。
李強指出,中法、中歐各有優勢,要進一步加強合作,在深化核能、航空航天等傳統領域合作的同時,挖掘在環保、數字經濟、人工智能、先進制造等新興領域合作潛力,實現互利共贏。中方鼓勵中國企業赴法投資。歡迎法國企業分享中國發展機遇。
那么,核能為何可以成為兩國合作的第一關鍵詞呢?
高盧人的核電驕傲
堅定自主發展核能這個點上,法國人和中國人都有自己的驕傲和堅持,這也許能一起合作這么久,很重要的一個三觀相符。
從戰后重建開始,不論是戴高樂還是密特朗,法國領導層從未放棄對核能的專注。
即使在2011年日本福島核事故發生后,各國民心動搖,談“核”色變,法國不為所動,持續下注核電。
十年后的今天,歐洲各國又因為激進的清潔能源政策被天然氣價格綁架,依靠核電長期出口電力的法國,已經成為了歐洲電力的救世主。
從客觀環境考慮,能源領域留給法國的,只有核電一條路。
歷史上曾經由于煤炭問題與鄰國產生沖突。石油方面原本可以依靠阿爾及利亞,但戰后的殖民地民族解放運動,也讓該國和法國脫離了聯系。
作為在歐洲有著重要影響力的工業大國,法國建國初期的能源供給,面臨著極大的壓力。

圖左為讓·弗雷德里克·約里奧-居里
1945年,法國總統戴高樂成立了法國國家原子能委員會(CEA),專門進行核能開發。這家官方機構的領導人,正是居里夫人的女婿,錢三強的導師——讓·弗雷德里克·約里奧-居里。法國人對能源自主的渴望,由此可見一斑。
經過十余年的研究,1956年,法國人開發了屬于自己的石墨氣冷反應堆。作為最基礎的反應堆,它采用石墨作為核反應的減速劑,可以使用廉價的天然鈾。然而早期的氣冷堆效率太低,使用石墨做減速劑,后續運營成本相對較高。(注:和中國早期研究熔鹽堆很類似)
CEA因此轉變技術路線,尋求更高效的核反應堆技術。
1958年,在CEA和法國電力(EDF)的主導下,法國從美國西屋引進了更加成熟和高性價比的壓水堆的技術。
法國在消化壓水堆的技術之后,確定了壓水堆主導的核能發展路線。1964年,法國第一座商用核電站落地,整個國家的主要能源向核能轉型。
然而讓法國領導層死磕核電的,不是核能技術,而是石油禁運。
1973年,國際石油危機爆發,名義油價和實際油價相差300%,“用油發電”已經成為絕路。時任法國總理梅斯梅爾因此提出了一個極端的思路:
用10年時間修80座核電站,到2000年修170座。盡管法國核電站達不到梅斯梅爾預期的上百座,但是就算是幾十座核電站,也能滿足法國能源獨立的需求。
法國的核電行業總體是國家主導,負責發電的法國電力,由法國政府持股85%。CEA負責核能發展戰略,可以看做是法國核能的“發改委”。在管理結構上,實際上國家間接管控整條核電產業鏈。
法國是核電發電量占總量比例最高的國家,整個法國電網約等于一張核電網。
放到現在來看,法國孤注一擲專精核電,恰恰是走對了最關鍵的一步棋。目前歐洲各國新能源政策過于激進,讓整個國家的國民生活,對特定資源產生嚴重依賴。歐洲去年的天然氣短缺,就離不開一系列激進政策的影響。
中法核能合作由來已久
中法在核電領域的合作歷史悠久。如果你深入了解中國核電的發展歷史,會發現除了我們自力更生,從軍用核能領域一步步實現民用核能以外,法國人在中國核電獨立自主的路上幫了不少忙。
因為核電是一個很復雜的領域,涉及技術領域很多,自己搞不定的可能就得找老師去請教。
錢給到位了,法國人很愿意教中國人本領,這個在今天西方國家嚷嚷脫鉤的背景下似乎不可思議,但在當年沒什么大不了的。
法國人希望伴隨中國經濟增長、能源需求增長、核電建設需求增長的東風,一起成長,把中國當做最重要的一塊海外市場。
我們師夷長技不是為了制夷,而是展開以我為主的多邊合作,互惠互利。
從核電的角度切入,去看法國電力在中國幾十年的發展,管中窺豹,你就能看明白,為什么以法國為代表的歐洲國家不愿意做美國的附庸,為什么他們不愿意同中國完全脫鉤。

1973年,法國蓬皮杜總統訪問中國,這是第一位訪問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歐洲國家元首。他的來訪推動了中法兩國在核能領域建立起一系列的接觸。
整個20世紀70年代,法國領導人多次訪華,其中一項重要議題就是中國的核電項目。
其實法國人很早就開始準備了,因為法國壓水堆技術源自美國,法國領導人還跑到華盛頓,找吉米·卡特開了綠燈,批準法國向中國出口核電設備。
法國駐華使館里甚至專門設了一個職位,叫“核電專員”,當時的專員中文名叫顧華年。
同一時期,中國的工程師也對壓水堆技術進行了大量深入的研究。
很快,合作的契機出現在了廣東,這片改革開放的熱土。
廣東想要發展經濟,必須解決能源供應問題。
煤炭資源在北方,優質水電資源在西南,風電光伏那時還沒發展起來,廣東迫切地需要核電,但發展核電需要大把大把的錢。
于是一家美國咨詢公司,名叫吉布斯·希爾,向廣州市領導人提出了一個想法:從外國貸款建設,賣電給香港還債——因為香港也有對電力的旺盛需求。
借錢買雞,養雞生蛋,賣蛋還錢,還有錢花。
所以在國家計委的投資項目表上,大亞灣核電站一欄的投資金額是“零”。

在廣東、香港以及一些在當地活躍的外國友人的共同支持下,1980年,中央財經委員會召開會議,遵照鄧公的指示,宣布在東南沿海至少建設兩座核電站。
大亞灣核電站預計造價高達40億美元,幾乎相當于當時中國外貿進出口總額的20%。
當時我們還不被允許向國際市場貸款,國家外匯儲備只有1.67億美元。
所以我們需要通過核電設備供應商提供的出口信貸,來推動這座核電站工程的實施。
選定外國設備的過程中,中方迅速鎖定了法國和英國的設備。
法國的建設成本比競爭對手低一半,而法國對中國早早表現出的友善態度,在核電領域的開放態度,博得了很多中方領導的好感。
緊接著,法國總統密特朗訪問中國,受到鄧公的接見。
密特朗表示:只要中國購買足夠數量的法國設備,法國能接受中國技術轉讓的要求。
同一天,兩國簽署的核電合作備忘錄中,法國保證在中國企業的參與下建設四個核反應堆,并同時向中國轉讓全部技術。

1986年夏天,大亞灣核電站正式開工,來自22個國家的1萬多人參與建設。
后來參與大亞灣項目的很多國人,都成為中國核電工業的中堅力量。特別是“黃金人”。

這是20世紀80年代大亞灣核電站赴法培訓人員的形象比喻,在當時國家外匯非常緊張的情況下,這些人平均每人培訓費約130萬法郎,按當時的金價計算,可以購買50公斤黃金,相當于一個成年人的體重。由于培訓代價不菲,所以后來大家稱他們是“黃金人”。
第一代“黃金人”都成為了我國核電發展的“種子隊”
1994年春,國務院批準15年內在廣東興建10臺核電機組,滿足中國經濟第一大省不斷增長的能源需求。
其中第二座廣東核電站將建設四臺100萬千瓦機組。
這一次,中方已經充分汲取了在大亞灣項目管理和建設中的豐富經驗,提出了“四個自主化”:自主設計、自主制造、自主建設、自主運行。
在大亞灣時期,核電設備國產化率不足1%,而在嶺澳一期,很多設備制造和設計工作都在中國完成,中國的設計院所擔當主力。最后電站的整體國產化占比迅速提高到30%,其中核島輔助系統達到50%。到后來“華龍一號”示范工程防城港二期,設備國產化率已經達到86.7%。
這時起,法國電力一方面出任業主咨詢顧問,另一方面開始參股中國的核電項目:和中方一起投資電力行業,共享收益,共擔風險。
后來,就有了這么個形象的說法:從老師到伙伴。
而這一切都發生在你情我愿的商業合同基礎之上,也發生在中法兩國長期友好互信的關系基礎之上。
借用1997年法國總統希拉克對中國做出的承諾:
“協助建立一個中國的民族工業。”
這句話不用過度美化,因為法國也想從中國的經濟、工業、能源發展中分一杯羹。
開門做生意,你愿意教,我愿意學,我學會了你再找找我們家別的生意,我們接著合作。
哪些項目會迎來新的變化
那這次原則性的申明,會惠及哪些核能項目得以加速或者上馬呢?

早在今年早些時候馬克龍訪華時,中法兩國在北京發布《中華人民共和國和法蘭西共和國聯合聲明》,其中關于民用核能合作的內容如下:
為實現能源體系低碳轉型的共同愿望,中法兩國在政府間和平利用核能合作協定框架下,開展民用核能務實合作。兩國致力于在中國國家原子能機構和法國原子能和替代能源委員會協議等基礎上,繼續推進在核能研發領域前沿課題上的合作。兩國支持雙方企業研究在核廢料后處理等問題上加強工業和技術合作的可能性。

早在2015年06月30日,中法兩國就在巴黎簽署了《深化民用核能合作的聯合聲明》,感興趣的可以通過閱讀原文查閱。
其實說白了,舊的版本里主要涉及三個主要項目
臺山EPR核電
英國新建核電項目
800噸核循環項目
分開說下
1. EPR
這是法國三代核電技術的“拳頭”產品,但是也全靠中國這座“后來居上”的全球首堆撐住了面子,成為世界EPR核電工程的領跑者和標桿。
臺山1、2號機組預計分別將于2018年、2019年投入商運,均領先于早先開建的芬蘭和法國的EPR項目。
同時,這也是中法兩國元首共同見證的元首工程。
但是后續是否在新建廠址或者擴建廠址繼續核準EPR堆型,從目前公開信源來看,熱度似乎并不是那么的高。
2. 英國新建項目
這個就... 不多說了
反正耿爽在聯合國直接表示我們支持阿根廷的馬島主權,這個基本和英國之間就有點鬧得不開心了,這個項目就算將來還有希望,那估計也是很久很久以后了。
3. 800噸核循環項目
上世紀80年代,我國確定了核燃料“閉式循環”與“發展核電必須相應發展后處理”的技術路線。“后處理+快堆”的多次核循環系統,正是我國核能發展“壓水堆——快堆——聚變堆”三步走的第二步目標。在近兩年出臺的《國民經濟“十三五”規劃》《“十三五”生態環境保護規劃》《能源技術革命創新行動計劃》《能源技術革命重點創新行動路線圖》《“十三五”核工業發展規劃》《核安全“十三五”》等一系列規劃中,核循環產業始終是高頻詞。數據顯示,一臺百萬千瓦壓水堆核電機組每年產生約20-25噸乏燃料,按目前我國核電規劃預測,到2030年將累計產生23500噸乏燃料,離堆貯存需求將達到15000噸,核電規模化發展必然要求進一步加快核燃料循環產業發展。但現實是,我國近年來雖然在乏燃料后處理技術基礎能力建設和核心技術自主創新方面取得了重要突破,但后處理技術整體上仍落后于世界核能強國。這個行業內簡稱“800噸”的中法合作建設項目,將參照法國阿格核循環廠,由國家專項基金投資,總投資超千億元。但是因為要價太高了,多年的拉鋸戰依然沒有落下塵埃。
馬克龍4月訪華的公開申明中,就有很明確的這么一句:“兩國支持雙方企業研究在核廢料后處理等問題上加強工業和技術合作的可能性。”
所以,如果要說那個能加速落地,個人淺薄的認為 800噸項目的可能性更高一丟丟。
當然,這年頭讓中國人繼續當冤大頭的可能性也進一步降低了。
最后說個細節:
值得一提的是:馬克龍作為核能的鑒定推崇者,提出了“核能復興”的計劃,而作為元首之間的合作橋梁,核能將在李強總理任期內,是很重要的一張牌。
讓我們拭目以待吧。
免責聲明:本網轉載自合作媒體、機構或其他網站的信息,登載此文出于傳遞更多信息之目的,并不意味著贊同其觀點或證實其內容的真實性。本網所有信息僅供參考,不做交易和服務的根據。本網內容如有侵權或其它問題請及時告之,本網將及時修改或刪除。凡以任何方式登錄本網站或直接、間接使用本網站資料者,視為自愿接受本網站聲明的約束。